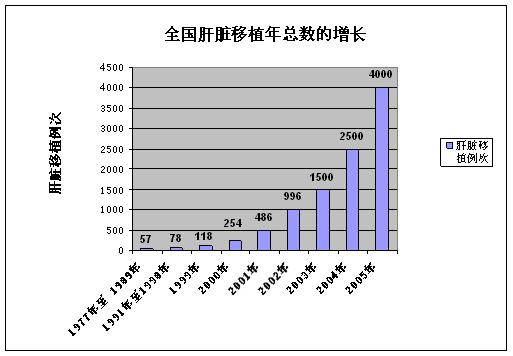七
俗話說得好:「福無雙至,禍不單行。」鬥爭會剛剛結束不久,張恒直好不容易地寫出了一封詳盡的長信,正在幻想著市委來給他甄別、平反,生活裏又發生了一椿事。此刻他緊皺著兩道眉毛在讀信:
恒直吾兒:
光陰似箭,日月如梭。汝高升農場,凡八個月有餘。汝父三個月前貴恙在身,臥床不起。余曾多次函告,囑汝寄款療治,唯迄今未見分文,亦無一字答復,不知何故?餘殊念!
汝父於今日淩晨四時許歸天。現遺體停放家中,無錢善後。闔家悲痛欲絕,焦急如焚。望汝見字後,速交三弟六十元,以購置棺柩料理後事,盡汝孝子之心。另交三弟十二元八角五分購買火車票,外加一元路途開銷,並督其速返,不得在外延誤。切切!
母字
三弟:恒旺
五弟:恒貴
二妹:恒榮
四妹:恒貞
五妹:恒娟
七妹:恒豔
又,本村郭先生,為人忠厚可靠,學問既淵且博,一向對餘家幫助甚大,餘感激不盡。汝當銘記在心,多加提攜,於適當時機,代其在外謀個一官半職。
母囑
信是母親央求本村小學教員郭先生寫的。母親還拉著弟妹們的手在各人的名字下面按上了自己的手指印。於是三弟懷裏揣著這封信,背上一袋山芋幹和蘿蔔乾作口糧,買了一張月臺票混上火車,千里迢迢地找他來了。——這個主意也是郭先生給出的:他一口咬定張恒直現在在農場當場長,而且還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,因為鈔票都花在時髦的老婆身上了,所以這八個月來沒有給家裏寄過一分錢。這位吃不起葷菜而又對魚肉饞涎欲滴的郭先生,在寫信的時候不斷提醒自己:他是一個老幹部。他又上過大學。哼!場長還嫌小,將來該當縣長!
張恒直呆呆地把這封信反復看了好幾遍,終算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。於是他把信揉成一團,隨手往褲袋裏一塞。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站在旁邊察顏觀色,這時便搶先開口說:
「爹死得好苦啊!家裏沒錢買棺材。」
三弟說話的聲音很低,好像是用鼻子哼出來的。他還不住地用手摸摸自己的眼睛,希望能在大哥面前摸出幾滴眼淚以表示他的悲傷。其實,這小夥子的靈魂深處卻在發笑:老骨頭死得太好了,現在不會再有人任意打罵他了吧?他是完全的自由了。
張恒直的眉毛愈皺愈緊。他繃著臉冷冰冰地說:
「死了就死了,一個富農分子又有什麼了不起的!」
這個回答叫三弟吃了一驚,但他馬上根據自己的心理去體會對方的感情,暗暗想道:「老骨頭呀,你在我們身上作孽太多,不是打就是罵,死了活該沒人疼。」於是他也索性撕下悲哀的假面具,伸出手向大哥要錢:一共是七十三元八角五分。這個數目字他早已背得滾瓜爛熟。
「我哪有錢啊!」大哥說,嘴唇哆嗦著,那張粗糙憔悴的黑臉變成了土灰色。停了一會兒,又補充道:「我一個錢也沒有。誰叫你來的?!」
三弟怎麼會知道呢?大哥每天吃的是最便宜最粗簡的飯食,吃一頓飯常常要算了又算,惟恐多花了一分錢;就是這樣,一個月還是剩不下幾毛錢。他想起了村裏郭先生的話,再看看大哥現在一副懊喪的倒楣相,還以為故意撒謊耍手段來騙他鄉下人。他的心陡地激怒了。他剛剛經歷了白坐火車的風險,認為自己有了不起的本領,豈能受自己老大的誑騙!他決心要拿點厲害出來和大哥幹一場:反正理在他身上,到哪兒去評理也不能不給錢啊!
「娘叫我來的。」三弟理直氣壯地說,希望自己的聲音讓附近所有的人都聽見。「你在外頭當幹部,不給家裏捎一個銅板回去,講理不講理!」
「誰不講理!」大哥火了,跺著腳說。「沒有錢就是不講理?」
「人民政府的幹部得講理。自己的親爹死了,屍首放在家裏爛著,不該掏些腰包出來買棺材給埋了?」
「我有腰包可掏嗎?你到這裏來也不事先寫封信問問。」
「娘托郭先生給你寫過一大疊信,你被狐狸精迷住了心竅,一封信也不回。爹死了沒錢買棺材,娘在家裏哭得眼睛像燈籠,你說我該來不該來?」
周圍漸漸地圍上了一些人,其中興趣最濃的是江濤。這時正是吃晚飯的時候,江濤顧不得吃,手裏捏著一個窩頭,湊上來向三弟關心地問長問短,打聽事情的根由。張恒直閉緊兩片嘴唇默然不語地站著。三弟激動的心也開始冷靜了下來。口角停止了。現在一個失望,一個頹喪,兩個人站在不同的地位,都在為了一個「錢」字煩惱著。多虧江濤出力,自告奮勇地向隊長說明了實情,把三弟安排在馬號裏宿了一夜。這一夜弟兄兩人都沒有睡好。三弟有三弟的使命和小算盤,大哥有大哥的困難和苦楚。
張恒直來到農場後,只給家裏去過一封短信,簡單地說明了自己的去向,關照家裏以後寫信不要再往大學寄了,其他什麼也沒有寫。家裏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受了處分。父親患病以後,母親先後給他來過四封信。他因為無錢可寄,乾脆一封也不回復。老實說,他根本就不曾把老子的病放在心上。現在人已經死了,他也不感到悲痛。他是在父親的拳頭和棍棒下長大的,自小就恨透了這位家庭暴君。他和那一大幫弟弟妹妹也談不上有什麼感情:他離開家的時候他們都很小,有的還沒有出生。現在彼此甚至連最起碼的瞭解都沒有。如果說他也像別人一樣有過值得記憶的童年,那全得歸功於母親。有一年除夕,他不小心碰碎了油瓶。父親勃然大怒,認為觸犯了灶菩薩,立刻把他關到地窖裏,揚言要活活地餓死他。母親瞞著父親烙了一個大餅子,偷偷地送到地窖裏給他吃。為了逃過父親尖利的眼睛,母親把餅子巧妙地藏在自己胸脯上。當她解開衣襟,灼熱的餅子已經燙傷了她的皮膚。當時母子兩人在陰暗寒冷的地窖裏抱頭痛哭了一場。這幕情景他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。……
母親是聯結全家的樞紐。張恒直在機關裏工作的時候,曾經不止一次地下過決心:和那個富農家庭脫離關係,把母親單獨接出來住。但是母親說什麼也不願意扔下丈夫和一大群子女的拖累,自己一個人跑到外面去和大兒子過清閒的日子。他不明白母親為什麼待父親那麼好,雖然她自己就是父親暴虐的最大受害者。他只好遵從母親的意志。那時侯他的工資比較高,生活又很簡樸,但仍然沒有一點積蓄,因為他把剩餘的錢全部寄回家裏去了。這也是為了母親的緣故。他希望減輕母親的負擔,希望她生活儘量過得好一些,雖然他很清楚:寄回去的錢約有一半是被父親搶去和酒友一起喝掉了,另一半都用在那一幫自私自利的弟弟妹妹身上。母親自己是一個小錢也捨不得花的。現在父親死了,母親「哭得眼睛像燈籠」——三弟這句話打中了要害,在大哥腦子裏不住地盤旋著。無論如何,他得想辦法給家裡弄些錢回去。
可是到哪裡去弄呢?大學裏對調幹學生有特殊照顧,遇到這類事照例是可以申請補助的。但是他離開學校已經八個月了,最近又剛被鬥過,他不好意思厚著臉皮去申請。而且,他現在頭上戴著一頂帽子,他知道申請也是白搭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,他躺在鋪上左思右想,最後想到了小王。
小王,指的是王本湘。他過去和張恒直的交情著實不淺。不論大事小事,甚至於夫妻之間的私事,他都要向自己的入黨介紹人張恒直「彙報」,徵求張恒直的意見。後來張恒直被劃為右派,王本湘在鬥爭會上一次再次上臺發言揭發,聲淚俱下,比其他幾名積極分子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話雖如此,可是私下裏對張恒直仍然很客氣,照樣老張長老張短地叫得很親熱。張恒直臨走的前一天,小王說了許多寬慰的話,最後還表示倘若老張以後經濟上有困難,可以找他小王幫忙。看來小王到底還是瞭解老張的,他們兩個人曾經一起向北大的右派分子作過鬥爭哩!他在寫給市委的信裏不就是舉出小王作證人的嗎?再說,小王愛人在醫院裏當會計,一個月掙六、七十元錢;小王自己每月也有二十五元調幹助學金。兩個人生活過得挺闊綽,銀行裏放著好幾百元現成的存款,借他幾十該不成問題吧?
第二天大清早,張恒直向隊長請准了假,滿懷希望地登上了長途汽車:他要到學校裏去找小王幫忙。
小王還是住在原來的宿舍。張恒直很順利地找到了他。他正躺在床上抽煙想心事,一看見張恒直,立刻就從床上跳起來,態度依然是那麼親熱,只不過把老張的「老」字去掉了:
「啊呀!是你呀,張恒直!是什麼風把你給吹來的啊?快請坐!快請坐!農場那裏空氣一定很新鮮吧?你現在身體鍛煉得多棒!又黑又結實,將來做個能文能武的新型知識份子,真叫人看了羡慕。現在大學裏也經常勞動,你回來准能做我們的老師。我已經下定決心:畢業後就到農村去勞動,在泥巴裏滾上千百次,一輩子跟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。」
王本湘又是搬凳子,又是倒開水,還遞給張恒直一支香煙,雖然他知道對方是從來不抽煙的。張恒直機械地接過了香煙,手指不斷地撚弄著它,一面結結巴巴地說明了來意。王本湘一聽說要向自己借錢,臉上和顏悅色的表情倏地消失了,一塊塊的肌肉變得很僵硬。
「難道組織上不管你們的生活嗎?有困難應該多找組織談談。再說,生活還是艱苦些好,這樣更有利於你的改造。」
張恒直低著頭,眼睛呆呆地望著手中那根細長的棒狀香煙,停了老長時間,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自己借錢的原因。王本湘臉上僵硬的肌肉逐漸緩和了下來。他似乎很同情張恒直的不幸,說了不少寬慰的話,最後才抱歉地說:
「我愛人上個月生病住醫院,一花就是幾百元。大前天我的一個表哥路過這兒,又向我要去了一百元。真是太不巧了!要是你早來一個星期就好了。要不,你把我這個錶拿去賣了……」
王本湘已經開始摘手錶,張恒直搖搖頭說:
「不用了,我回去再想想別的辦法吧。」
「你先回去向別人借一下吧,過幾個月我代你還。」王本湘說,把剛才摘下的手錶又重新戴在手上。「這個錶也值不了多少錢,而且還未必馬上就能賣出去。」
張恒直知道自己該走了,但他忽然想起給市委寫的信,於是又站住了。
「我還有一件事想和你談一談。」
「什麼事?」王本湘說,眼睛盯著手錶。「吃完飯再談吧。現在改成了食堂制,去晚了要排很長的隊。你先在這兒坐一會,我買了飯就回來。」
王本湘一去總不回來。張恒直像一塊木頭似地端坐在凳子上等著。同室的人吃過午飯都陸續回來休息了。他見到這些熟人,心裏很不是滋味,也不知道該不該和他們打個招呼問句好。倒是一個一向被他瞧不起的「落後分子」(他差一點被打成了右派)實在看不過去,特地再跑到食堂給他端來了一份菜和兩個饅頭。
(待續)
(http://www.dajiyuan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