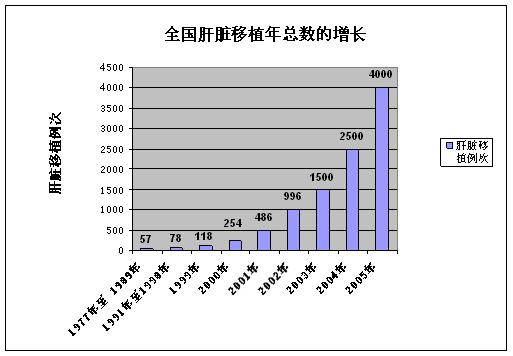七
俗话说得好:“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”斗争会刚刚结束不久,张恒直好不容易地写出了一封详尽的长信,正在幻想着市委来给他甄别、平反,生活里又发生了一椿事。此刻他紧皱着两道眉毛在读信:
恒直吾儿: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汝高升农场,凡八个月有余。汝父三个月前贵恙在身,卧床不起。余曾多次函告,嘱汝寄款疗治,唯迄今未见分文,亦无一字答复,不知何故?余殊念!
汝父于今日凌晨四时许归天。现遗体停放家中,无钱善后。阖家悲痛欲绝,焦急如焚。望汝见字后,速交三弟六十元,以购置棺柩料理后事,尽汝孝子之心。另交三弟十二元八角五分购买火车票,外加一元路途开销,并督其速返,不得在外延误。切切!
母字
三弟:恒旺
五弟:恒贵
二妹:恒荣
四妹:恒贞
五妹:恒娟
七妹:恒艳
又,本村郭先生,为人忠厚可靠,学问既渊且博,一向对余家帮助甚大,余感激不尽。汝当铭记在心,多加提携,于适当时机,代其在外谋个一官半职。
母嘱
信是母亲央求本村小学教员郭先生写的。母亲还拉着弟妹们的手在各人的名字下面按上了自己的手指印。于是三弟怀里揣着这封信,背上一袋山芋干和萝卜干作口粮,买了一张月台票混上火车,千里迢迢地找他来了。——这个主意也是郭先生给出的:他一口咬定张恒直现在在农场当场长,而且还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,因为钞票都花在时髦的老婆身上了,所以这八个月来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。这位吃不起荤菜而又对鱼肉馋涎欲滴的郭先生,在写信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:他是一个老干部。他又上过大学。哼!场长还嫌小,将来该当县长!
张恒直呆呆地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好几遍,终算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他把信揉成一团,随手往裤袋里一塞。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站在旁边察颜观色,这时便抢先开口说:
“爹死得好苦啊!家里没钱买棺材。”
三弟说话的声音很低,好像是用鼻子哼出来的。他还不住地用手摸摸自己的眼睛,希望能在大哥面前摸出几滴眼泪以表示他的悲伤。其实,这小伙子的灵魂深处却在发笑:老骨头死得太好了,现在不会再有人任意打骂他了吧?他是完全的自由了。
张恒直的眉毛愈皱愈紧。他绷着脸冷冰冰地说:
“死了就死了,一个富农分子又有什么了不起的!”
这个回答叫三弟吃了一惊,但他马上根据自己的心理去体会对方的感情,暗暗想道:“老骨头呀,你在我们身上作孽太多,不是打就是骂,死了活该没人疼。”于是他也索性撕下悲哀的假面具,伸出手向大哥要钱:一共是七十三元八角五分。这个数目字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。
“我哪有钱啊!”大哥说,嘴唇哆嗦着,那张粗糙憔悴的黑脸变成了土灰色。停了一会儿,又补充道:“我一个钱也没有。谁叫你来的?!”
三弟怎么会知道呢?大哥每天吃的是最便宜最粗简的饭食,吃一顿饭常常要算了又算,惟恐多花了一分钱;就是这样,一个月还是剩不下几毛钱。他想起了村里郭先生的话,再看看大哥现在一副懊丧的倒楣相,还以为故意撒谎耍手段来骗他乡下人。他的心陡地激怒了。他刚刚经历了白坐火车的风险,认为自己有了不起的本领,岂能受自己老大的诳骗!他决心要拿点厉害出来和大哥干一场:反正理在他身上,到哪儿去评理也不能不给钱啊!
“娘叫我来的。”三弟理直气壮地说,希望自己的声音让附近所有的人都听见。“你在外头当干部,不给家里捎一个铜板回去,讲理不讲理!”
“谁不讲理!”大哥火了,跺着脚说。“没有钱就是不讲理?”
“人民政府的干部得讲理。自己的亲爹死了,尸首放在家里烂着,不该掏些腰包出来买棺材给埋了?”
“我有腰包可掏吗?你到这里来也不事先写封信问问。”
“娘托郭先生给你写过一大叠信,你被狐狸精迷住了心窍,一封信也不回。爹死了没钱买棺材,娘在家里哭得眼睛像灯笼,你说我该来不该来?”
周围渐渐地围上了一些人,其中兴趣最浓的是江涛。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,江涛顾不得吃,手里捏着一个窝头,凑上来向三弟关心地问长问短,打听事情的根由。张恒直闭紧两片嘴唇默然不语地站着。三弟激动的心也开始冷静了下来。口角停止了。现在一个失望,一个颓丧,两个人站在不同的地位,都在为了一个“钱”字烦恼着。多亏江涛出力,自告奋勇地向队长说明了实情,把三弟安排在马号里宿了一夜。这一夜弟兄两人都没有睡好。三弟有三弟的使命和小算盘,大哥有大哥的困难和苦楚。
张恒直来到农场后,只给家里去过一封短信,简单地说明了自己的去向,关照家里以后写信不要再往大学寄了,其他什么也没有写。家里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受了处分。父亲患病以后,母亲先后给他来过四封信。他因为无钱可寄,干脆一封也不回复。老实说,他根本就不曾把老子的病放在心上。现在人已经死了,他也不感到悲痛。他是在父亲的拳头和棍棒下长大的,自小就恨透了这位家庭暴君。他和那一大帮弟弟妹妹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:他离开家的时候他们都很小,有的还没有出生。现在彼此甚至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。如果说他也像别人一样有过值得记忆的童年,那全得归功于母亲。有一年除夕,他不小心碰碎了油瓶。父亲勃然大怒,认为触犯了灶菩萨,立刻把他关到地窖里,扬言要活活地饿死他。母亲瞒着父亲烙了一个大饼子,偷偷地送到地窖里给他吃。为了逃过父亲尖利的眼睛,母亲把饼子巧妙地藏在自己胸脯上。当她解开衣襟,灼热的饼子已经烫伤了她的皮肤。当时母子两人在阴暗寒冷的地窖里抱头痛哭了一场。这幕情景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……
母亲是联结全家的枢纽。张恒直在机关里工作的时候,曾经不止一次地下过决心:和那个富农家庭脱离关系,把母亲单独接出来住。但是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扔下丈夫和一大群子女的拖累,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和大儿子过清闲的日子。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待父亲那么好,虽然她自己就是父亲暴虐的最大受害者。他只好遵从母亲的意志。那时侯他的工资比较高,生活又很简朴,但仍然没有一点积蓄,因为他把剩余的钱全部寄回家里去了。这也是为了母亲的缘故。他希望减轻母亲的负担,希望她生活尽量过得好一些,虽然他很清楚:寄回去的钱约有一半是被父亲抢去和酒友一起喝掉了,另一半都用在那一帮自私自利的弟弟妹妹身上。母亲自己是一个小钱也舍不得花的。现在父亲死了,母亲“哭得眼睛像灯笼”——三弟这句话打中了要害,在大哥脑子里不住地盘旋着。无论如何,他得想办法给家里弄些钱回去。
可是到哪里去弄呢?大学里对调干学生有特殊照顾,遇到这类事照例是可以申请补助的。但是他离开学校已经八个月了,最近又刚被斗过,他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去申请。而且,他现在头上戴着一顶帽子,他知道申请也是白搭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他躺在铺上左思右想,最后想到了小王。
小王,指的是王本湘。他过去和张恒直的交情着实不浅。不论大事小事,甚至于夫妻之间的私事,他都要向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恒直“汇报”,征求张恒直的意见。后来张恒直被划为右派,王本湘在斗争会上一次再次上台发言揭发,声泪俱下,比其他几名积极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话虽如此,可是私下里对张恒直仍然很客气,照样老张长老张短地叫得很亲热。张恒直临走的前一天,小王说了许多宽慰的话,最后还表示倘若老张以后经济上有困难,可以找他小王帮忙。看来小王到底还是了解老张的,他们两个人曾经一起向北大的右派分子作过斗争哩!他在写给市委的信里不就是举出小王作证人的吗?再说,小王爱人在医院里当会计,一个月挣六、七十元钱;小王自己每月也有二十五元调干助学金。两个人生活过得挺阔绰,银行里放着好几百元现成的存款,借他几十该不成问题吧?
第二天大清早,张恒直向队长请准了假,满怀希望地登上了长途汽车:他要到学校里去找小王帮忙。
小王还是住在原来的宿舍。张恒直很顺利地找到了他。他正躺在床上抽烟想心事,一看见张恒直,立刻就从床上跳起来,态度依然是那么亲热,只不过把老张的“老”字去掉了:
“啊呀!是你呀,张恒直!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啊?快请坐!快请坐!农场那里空气一定很新鲜吧?你现在身体锻炼得多棒!又黑又结实,将来做个能文能武的新型知识份子,真叫人看了羡慕。现在大学里也经常劳动,你回来准能做我们的老师。我已经下定决心:毕业后就到农村去劳动,在泥巴里滚上千百次,一辈子跟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。”
王本湘又是搬凳子,又是倒开水,还递给张恒直一支香烟,虽然他知道对方是从来不抽烟的。张恒直机械地接过了香烟,手指不断地撚弄着它,一面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。王本湘一听说要向自己借钱,脸上和颜悦色的表情倏地消失了,一块块的肌肉变得很僵硬。
“难道组织上不管你们的生活吗?有困难应该多找组织谈谈。再说,生活还是艰苦些好,这样更有利于你的改造。”
张恒直低着头,眼睛呆呆地望着手中那根细长的棒状香烟,停了老长时间,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自己借钱的原因。王本湘脸上僵硬的肌肉逐渐缓和了下来。他似乎很同情张恒直的不幸,说了不少宽慰的话,最后才抱歉地说:
“我爱人上个月生病住医院,一花就是几百元。大前天我的一个表哥路过这儿,又向我要去了一百元。真是太不巧了!要是你早来一个星期就好了。要不,你把我这个表拿去卖了……”
王本湘已经开始摘手表,张恒直摇摇头说:
“不用了,我回去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”
“你先回去向别人借一下吧,过几个月我代你还。”王本湘说,把刚才摘下的手表又重新戴在手上。“这个表也值不了多少钱,而且还未必马上就能卖出去。”
张恒直知道自己该走了,但他忽然想起给市委写的信,于是又站住了。
“我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谈一谈。”
“什么事?”王本湘说,眼睛盯着手表。“吃完饭再谈吧。现在改成了食堂制,去晚了要排很长的队。你先在这儿坐一会,我买了饭就回来。”
王本湘一去总不回来。张恒直像一块木头似地端坐在凳子上等着。同室的人吃过午饭都陆续回来休息了。他见到这些熟人,心里很不是滋味,也不知道该不该和他们打个招呼问句好。倒是一个一向被他瞧不起的“落后分子”(他差一点被打成了右派)实在看不过去,特地再跑到食堂给他端来了一份菜和两个馒头。
(待续)
(http://www.dajiyuan.com)